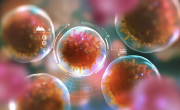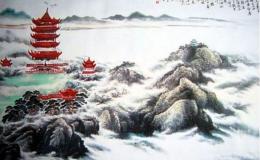博卡哈利:科技巨头窃取大选
“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发了这些方法来无形地影响人们,因为他们对我们、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的观点和兴趣以及我们的喜好和厌恶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如此了解,以至于他们正在建立模型来改变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看不见,我们被蒙在鼓里。”阿卢姆∙博卡哈利(Allum Bokhari)说。
大型科技公司究竟是如何影响用户的政治信仰的?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访问调查记者博卡哈利。他是《#删帖:大型科技公司抹杀川普运动和窃取大选之战》(#Deleted: Big Tech’s Battle to Erase the Trump Movement and Steal the Election)一书的作者。博卡哈利对大科技公司的内部人士进行了大量采访,以更多了解硅谷科技巨头如何影响用户、甚至选举。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大科技公司控制信息、影响大选且不被追责
杨杰凯:阿卢姆∙博卡哈利,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博卡哈利:很高兴能上你的节目。
杨杰凯:我要说,阿卢姆,你写了《#删帖》这本非常非常耐人寻味、非常及时的书。我想请你告诉我——其实你在这里审视的问题有很多。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科技公司的审查,这中间既有看得见的审查制度,也有你所说看不见的审查制度。但很多人心中的一大问题——你详细审视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一切和我们的选举过程有什么关系?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
博卡哈利:正如我在书中所涉及的那样首先,我要说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我对大科技公司的看法。它是根据我对脸书内部的人、谷歌内部的人、对这些公司的发展方向以及他们对民主政治影响——这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影响——感到忧虑的举报人进行的采访。对这些公司没有任何监督。
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的一件事是,2016年(川普的当选)改变了硅谷内部的一切,这些公司内部出现了巨大的恐慌。其中大部分公司——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真的倾向极左——它们没有想到川普会赢。2016年大选过后,反川普最积极的科技公司员工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力量,去制定反所谓的“错误信息”、反所谓的“假新闻”、反所谓的“仇恨言论”的各种计划。这就是这一切的开始。这种趋势开始加速。我认为,正如书中所说,其焦点一直在于扑灭川普运动,确保2016年(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
你可以说这是带有党派性的夸大之词。很多人说我的副标题“大科技公司抹杀川普运动和窃取大选之战”是危言耸听。但如果你看看过去两周发生的事件,我认为你不会把它叫做危言耸听。我们看到这些大科技公司在封杀美国最古老的报纸之一:《纽约邮报》。我们看到它们暂停了白宫新闻秘书的账户。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多次审查总统的账户。
它们在干什么非常清楚。它们有自己的居心。没有任何法规能阻止它们干涉选举,它们对信息流有强大的控制权。它们有动机使用这种权力。有没有监管机构阻止它们使用这种权力。我们马上就要进行2020年的关键选举,这将对美国人被允许看到什么、美国人被允许阅读什么有重大的影响。
硅谷环境极左 对用户实施奥威尔式洗脑
杨杰凯:你已经和许多业内人士、举报人都谈过了。在我们深入之前,你能否举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例子,他们告诉了你什么?
博卡哈利:好,我将重点谈谈我的一个脸书消息来源在书中告诉我的一件事——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去看看deletebook.com网站,那儿有一个完整的对此人和硅谷内部其他多人的详尽采访录像。
他告诉我的一件事是,2016年之后脸书的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去极端化”工作。脸书被媒体指责说它助长了“极度党派偏见”(hyper-partisanship,注:指政客不顾提案本身,单纯从政党利益考量,为反对而反对的这种态势)和“两极分化”(polarization)的文化。所以我的脸书消息来源告诉我,他们一直在关注那些在脸书上从所谓的“极右翼”走向“中间立场”的人,看他们读了什么、看他们看了什么样的视频。我的消息来源说,他们可以建立一个使用者模型来影响该平台上其他所谓的极右派人士。
当然,这就是硅谷。这是一个极左的环境。这一点连(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都承认,硅谷的环境极左,所以他们对“极右”的定义会和我们不同。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的大体要点是,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发了这些方法来无形地影响人们,因为他们对我们、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的观点和兴趣以及我们的喜好和厌恶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如此了解,以至于他们正在建立模型来改变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看不见,我们被蒙在鼓里。
我觉得这是非常奥威尔式的。似乎脸书正在努力开发一种洗脑模式,他们称之为“去极端化”。当然,这词听上去很动听,让它听起来是政治中立的:“我们只是想让每个人少些‘党派偏见’(partisanship),不要那么两极分化。”但我认为,这掩盖了一个非常阴险的计划。
杨杰凯:这完全取决于其设想的“中间立场”在“去极端化”努力中的位置。
博卡哈利:正是如此。我曾和脸书的人私下交流过,(那人是)左派脸书雇员。他们说:“‘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不是一个政治运动。每个人都应该认同它。我们不认为这和政治有关。”他们在女权主义和所有其它极左事务上都这么说。所以正如你所说,硅谷所认为的政治中间立场可能与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政治中间立场相去甚远。
谷歌影响用户:类似中共社会信用体系“品质排名”
杨杰凯:好吧,请进一步说说吧,这实在是非常耐人寻味。再跟我说说这种无形的影响是如何运作的。你说脸书创造模型,试图把人们转移到这个假设的“中间立场”,而我想这个“中间立场”是脸书的当权者决定的。但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你是否有一个例子——例如,一个实例——来说明这种无形的审查制度已经在实际中运用?事实上,我知道你有。你能否为我们解说一下?
博卡哈利:很难找到例子。但我们已经看到谷歌——虽然这是一个与脸书不同的公司,很明显——正在做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谷歌完全抹去了保守派媒体的链接,比如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我们在7月份公布的资料显示,与2016年同期相比,布莱巴特新闻链接在谷歌搜索的可见度下降了99%。他们已经完全封杀了布莱巴特新闻这个很棒的新闻机构。
我曾在那里工作了五年。他们(布莱巴特新闻)发布了我所有关于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独家新闻。他们刊登了我对川普总统的独家采访。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这些头条新闻,你甚至找不到它们,包括我对总统的独家采访。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尚未决定选谁的选民,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乔∙拜登或唐纳德∙川普的信息、甚至是关于你当地选区候选人的信息,你要是(用谷歌),很可能找不到任何非进步主义、非“主流”、非企业化的媒体。这也是谷歌影响人们的一种方式,因为人们不会认为他们看到的搜索结果是有偏见的。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要的信息,所以他们的思辨能力并不像他们在阅读《纽约时报》的故事或阅读福克斯新闻的故事那样高度警觉。你知道在那些媒体上新闻背后有某种观点。人们不会对谷歌有这样的假设,这就是他们如何在无形中影响人们。
杨杰凯:这一点让我想起了罗伯特∙爱泼斯坦博士的研究。至少在谷歌方面,他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在展示搜索结果相对排名的重新排序对用户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有关政治候选人的结果。它实际上会显著影响人们会如何最终投票。
博卡哈利:绝对正确。他的研究显示,超过百分之十的未决定选民可能因为搜寻引擎结果而改变立场。这足以反转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而即将到来的2020年大选将是势均力敌的。我们确实要看看大科技公司是否能左右选举,它们肯定没有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过去两周。
但我非常想进入到其隐形审查制度的核心,因为它影响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所有一切。我重点关注它的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我在书中详细讨论了,就是“品质排名”(quality ranking)。“品质排名”是指你在推特或脸书上发布的所有内容,你在谷歌上尝试和输入的每一个网站,都会被赋予一个秘密分数。而这个分数就是这些平台的算法决定什么东西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顶部、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脸书、YouTube或推特时间线顶部。大科技公司就是通过这个分数对互联网上的大量内容进行排序,因为它们必须决定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时间线顶部。它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它们的方式就是“品质排名”。
在过去,“品质排名”曾只取决于一些相当简单和合理的因素。如果你的网站有恶意软体和病毒、如果有垃圾邮件或网络钓鱼或其它危险的材料,这会影响你的品质得分。你的网站可能不会出现在接近谷歌第一页结果的地方。推特和脸书也是一样——如果你的帖子包含不安全的素材,人们就不会看到。这算是合理的。
但在过去四年里,它们把各种政治判据也引入到了评分中。现在的算法需要考虑一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比如它们问,某网站或帖子或YouTube视频是否包含“错误信息”或“仇恨言论”或“假新闻”或“阴谋论”。所以现在这个“品质排名”部分是由你是否符合硅谷的价值观、是否符合统治精英的价值观来决定的。
我认为,这在我看来,这个系统正变得与中国(中共)的社会信用体系越来越像:你的排名也是根据你对统治精英价值观的符合程度。这基本上就是硅谷的发展方向。我们真的无法逃避,因为布莱巴特新闻在几个月前刊登了一个新闻,说所有这些公司在“仇恨言论”的共同定义上正在达成一致。它们在“错误信息”和“假新闻”、“阴谋论”上可能也会达成一致。所以即使在替代性平台上也将无法逃脱此劫。
脸书封杀亨特“电脑门”相关信息 完全放弃原则
杨杰凯:这真的很吸引人。你提到了最近发生的这一整套围绕亨特∙拜登电子邮件的审查行为。这非常有趣,因为我想甚至脸书的代表公开说,“甚至在事实核查之前,我们就要封杀这个报导”——不管所谓的“事实核查”有多可疑——但在我看来,如你所述,人们根据其价值观并做出决策似乎(被大科技公司视为)政治上的麻烦。
博卡哈利:是的。顺便说一句,脸书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放弃原则了。我们最近发表了一篇报导,揭露出脸书负责内容管制的全球总监安娜∙马坎朱(Anna Makanju)曾经是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高顾问。实际上,拜登与乌克兰政治高层人士的通话中,她有参与。她还在大西洋理事会任职——大西洋理事会,她是那里的研究员。大西洋理事会从《纽约邮报》报导中(拜登家族)丑闻的核心公司——布里斯马(Burisma)公司那里拿了四十多万美元。让这样的人在脸书内部担任如此高级的职位……顺便说一下,脸书没有对这个故事发表评论。他们完全沉默。他们完全想搪塞过去——这让我觉得是无可救药的让步、彻底的利益冲突。
就像你说的那样,脸书在过去四年里花了很多时间来建立这个审查机构处理所谓的“错误信息”和“假新闻”、建立这个第三方的事实核查员网络,他们居然绕过这个系统来封杀这个故事。因为此事,他们甚至受到(左派新闻研究机构)波因特研究所(Poynter Institute)的谴责,而该研究所认可了他们的第三方的事实核查员。这真的很离谱。即使对于脸书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前所未有的举动。
反建制独立媒体崛起 主流媒体欲用新闻审查重获控制权
杨杰凯:当然,就在我们录制本期节目的时候,昨天我们听到新闻说,(左派记者)葛籣∙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被他自己建立的媒体扫地出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建立该媒体正是为了直言不讳。我的意思是,这是他觉得他需要一个独立媒体的原因。似乎——我们还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媒体编辑们干脆拒绝刊登任何与拜登家族有关的负面新闻。
博卡哈利:这对主流媒体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威胁,因为突然间有独立博客、YouTubers、Periscope上的人可以和它们公平地竞争。对它们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过去,这些东西会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会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出去。在2016年正是这样。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如此卖力——这里的“它们”指的是科技公司和主流媒体,它们总是给科技公司施加压力,让它们做更多的新闻审查——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过去四年里一直在试图重新获得对这些平台的控制权。因为我认为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运动在2016年所展现的巨大声势是非常有威胁性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它们在过去四年里为建立这些系统、遏制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所做的所有工作的最终结果。
我不知道它们在封杀《纽约邮报》上是否成功。我认为《纽约邮报》的报导仍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虽然在脸书上和来自主流媒体的其它故事相比,它没有获得大范围的关注。但人们还是读到了它、还是分享了它、还是找到了它。但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封杀却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出名、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所谓外国干涉是欺骗 真正危险是科技公司的中共员工
杨杰凯:你谈到这些科技公司使用的信息或来源的评级系统,与中共一直在开发的“社会信用评级”非常相似。这让我想到,《纽约邮报》披露脸书存在一个小组,我记得这个小组叫做“仇恨言论管理”(Hate-Speech Engineering)小组,它里面有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的人(作为审查员)在对“仇恨言论”进行“管制”。你怎么看待这个现实或者说这个被揭露出的事情?
博卡哈利:这是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的。在书中,我的脸书消息来源也告诉我:脸书的很多外国员工将竭力对付“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看作他们影响美国选举的一种方式,因为脸书的外国员工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和脸书的美国员工一样,因唐纳德∙川普的获胜而感到挫败。
我还和瑞安∙哈特维格(Ryan Hartwig)谈过——他是脸书的举报人——他告诉我,他获得许可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选举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这真正显示了这些努力、这些媒体在过去四年里拚命地、竭尽全力地宣传的有关俄国、外国的干涉是个谎言。
但“外国干涉”的真正危险是所有为这些科技公司工作的外国员工,包括你说的中国员工。我们是否知道他们同仇敌忾是为美国的利益还是为中共的利益?我们不知道。就在上周,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委内瑞拉政府前特工的报导,他为该政府工作了很多很多年,现在为脸书工作。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关注这样的个人,这种有关“外国干涉”的恐慌完全是种骗人玩意儿。
两种审查工具:训练算法来识别言论类型和人际联系
杨杰凯:让我确认一下。你的论点是,对选举的最大干扰来源,没有之一,将是来自大科技公司。
博卡哈利:绝对是的。这就是原因:大科技公司已经能够阻止川普运动的势头。我再来详细分析一下。我已经提到了关于品质排名的问题。硅谷使用的另外两件工具我们也应该知道。它们审查武器库中还有两个关键工具:一个是网络分析,还有一个是语言分析。
你之前简单说过语言分析,即硅谷如何训练算法来识别某些类型的言论。比如训练算法来识别“仇恨言论”,训练算法来识别“错误信息”。脸书甚至在今年夏天举办了一场奖金10万美元的比赛,奖励那些设计出检测仇恨恶搞短片最佳方法的程序员。他们甚至在训练算法来识别图像。
还有网络分析,即硅谷训训练算法来识别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如谁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谁、谁和谁结成朋友。综合起来,这是一个审查和压制整个政治运动的模式。认真想想,一个大V在推特或脸书上因“仇恨言论”或“错误信息”而被禁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追随者可能不会被封杀。但是可能发生的是,一旦这个大V被禁,该平台就会给算法发出一个信号,说所有关注这个账号的人因为关注了一个已知的因发布“仇恨言论”或发布“错误信息”的账号而被打入另册。
虽然他们自己不会被禁,但他们的品质排名可能会下降,所以他们可能会较少出现在搜索中,他们可能会较少出现在脸书、推特的新闻源或其它任何硅谷技术平台对人们信息进行排名和分类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压制整个网络和整个政治运动的模式。我相信,这就是阻挡川普运动在2016年在数字世界中真正建立势头的原因。
杨杰凯:好,非常精彩。你是说你有证据表明,正是这些类型的系统在发挥作用?还是说这是根据其现今能力的理论推测?
博卡哈利:它们并没有试图隐藏。就像我说的,脸书甚至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个公开比赛的广告,让程序员训练算法来检测仇恨恶搞短片。因此语言分析的东西是公开的。
至于网络分析,所有大科技平台都在用。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网络分析”,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电脑科学领域。就像品质排名曾经被用于相当无害的目的,比如把含有病毒和恶意软体的网站排除在外一样,网络分析曾经被用于监测去快餐店Chick-fil-A的人的网络或者在亚马逊上购书者的网络。但当然现在这被用来作为反击“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的工具。
再说一次,这些公司对它们正在做什么非常公开。这些是它们用来做上述工作的工具。
大科技平台控制政治组织手段 川普政府力图遏制
杨杰凯:我在想,我们在准备这个访谈的时候我们私下谈了一些事情。我提到,我经常对一些保守派评论员在看到人们因为共和党人获胜或者类似的事情而不高兴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幸灾乐祸感到不快。因为看看这些人、特别是那些最流行的恶搞短片,这些人看起来真的受到了伤害,非常痛苦。当我看到这些视频时,我想到了控制信息能力的力量。跟我说说你在这方面的想法。
博卡哈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可以主张——社交媒体确实会让人两极分化。问题是,脸书似乎并没有去攻击那些使左派极端化的人,导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些时候人们谈到政治就完全失控。我不认为脸书应该操控任何人的政治。它们不应该去尝试和对任何人“去极端化”。但毫无疑问,这导致了这种趋势的恶化。
这其实不仅仅是社交媒体的问题,你要明白这些人是在大学校园里被灌输的。他们被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洗脑,从他们出生到大学毕业都在给他们灌输宣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关于大科技公司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我同意嘲笑这些人对政治的痴迷是有点残忍的,因为他们似乎真的相信美国即将陷入法西斯独裁,他们似乎真的很不安,就像你说的那样——问题在于,所有这些从校园里毕业出来的年轻人都完全极端化了,他们正在进入硅谷。
早在2018年,我获得了布莱巴特新闻上发布的谷歌高层对川普选举的反应视频,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崩溃了,他们在流泪。他们在谈论选举之后需要做什么。一位高管说,他想把民粹主义运动变成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这是他的原话。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说,他觉得川普当选令人反感,他把川普选民比作极端分子。
因此,嘲笑在视频中因川普当选而尖叫的随便哪个家伙是一回事,但当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公司领导人这样做时,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他们对选举、对政治信息、对新闻媒体有强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在美国,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杨杰凯:看着这些,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无奈,对吧?他们应该感到无奈吗?
博卡哈利:是,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况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大科技平台控制了政治组织的手段。今天大部分的政治言论、活动以及组织、大部分的草根活动都发生在这些平台上。所以你要试图组织起来反对它们,但它们控制了你要进行组织活动的平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另一个困难——在书中有一整章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是硅谷的游说资金在华盛顿特区泛滥:它们资助保守派机构;它们资助进步派机构;它们资助共和党政客;它们资助民主党政客。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有这些没完没了的委员会听证会,但国会在驯服这些科技巨头方面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的原因。
所以我现在非常悲观。但存在一丝希望:川普政府似乎在大科技公司的权力问题上采取了实际行动。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表示他们将考虑针对(《联邦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制定新的规则,这是一项允许科技公司审查几乎任何东西而不会导致任何法律后果的关键法律。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川普政府也任命了很多重要官员到联邦官僚机构中。比如内森∙西明顿(Nathan Simington)在社交媒体问题上非常出色,被任命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成员。亚当∙坎德布(Adam Candeub)是个优秀的言论自由律师——他参与过针对推特的言论自由案件——他被安排在联邦政府内部的一个重要位置,专门负责和这些科技巨头打交道。现在我们的行政部门似乎很认真地在处理这个问题。
问题是,谁会在几天后的选举中获胜?因为乔∙拜登会用同样的行政权力来迫使科技公司进行更多的审查。他在整个竞选活动中都在要求脸书对他的政治对手进行审查。如果他当选,这绝对会发生。所以互联网自由绝对是几天后大选中的议题。这是我认为人们可以参与的一件事。他们能做的最重要事情可能就是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去投票。
国会分裂无力监管科技巨头 公司权力来自第230条
杨杰凯:对于你的观点,我最近看到霍利(Josh Hawley)参议员——他似乎在呼吁国会说:“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他是联邦参议员,但是人们似乎有这种感觉——也许有些意外——立法部门针对所有这些问题缺乏行动。
博卡哈利:是的,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民主党人对大科技公司力量危险的反应基本上与共和党人完全相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夏威夷州众议员图希∙歌巴德(Tulsi Gabbard),她似乎理解审查问题。但大多数民主党人虽然在谴责科技平台,但他们谴责科技平台的理由与共和党人谴责科技平台的理由正好相反。
民主党人、大多数民主党政客在谈论科技巨头时,他们的论点是:“为什么你不审查更多的仇恨言论?你为什么不更严格地控制虚假信息?”而共和党人则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审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陷入僵局。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分裂的国会中获得多数。当一方希望科技公司停止审查时,另一方则希望它们审查更多。
杨杰凯:阿鲁姆,我们刚刚看到最近顶级科技巨头总裁参加的参议院听证会。被传唤去参加参议院听证会应该是一件让人产生敬畏的事情,因为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看了这些听证会,在我看来这些领导人似乎并不十分在意自己受到传唤。这可能只是我的印象。鉴于我们刚才谈到的一切,你预计这些参议院听证会会产生何种影响?
博卡哈利:我认为你是正确的。我相信他们并不害怕参议院,我想你也看到了,根据他们的举止,尤其是(推特CEO)杰克∙多西(Jack Dorsey)似乎在告诉参议院,“如果你不喜欢,就离开推特。”所以我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害怕立法者。他们不害怕国会。他们不怕参议院。他们知道这些人不会拿他们怎么样。他们知道针对他们的立法行动不会成功。他们知道他们送给保守派和民主党人的游说资金已经得到回报。我认为他们现在唯一害怕的政府部门是行政部门,因为在参议院或国会中根本没有足够的票数来驯服他们。
杨杰凯:你提到,一些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在说他们希望在某些领域有更严格的审查。在共和党方面,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讲自由市场——你怎么能试图限制一家公司的经营方式,对吗?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监管科技巨头,最近司法部发起了针对谷歌的反垄断诉讼。但是总的来说,国会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去监管。你有什么看法?
博卡哈利:是的。即使在共和党方面,虽然有一些好的参议员和共和党国会议员理解这个问题——像霍利、克鲁兹(Ted Cruz)、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这样的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不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反对监管科技巨头,因为他们还停留在1980年代的自由市场心态中。
也有很多共和党的保守派智库——比如传统基金会,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也在给他们灌输论点,说:“如果你干涉大科技公司,那么你就是在干涉自由市场。”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大科技公司目前的地位、目前的权力是拜《联邦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所赐,是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授予它们一个特权。所以,说干涉这个法律就是干涉自由市场,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这实际上是政府的施舍,是其它类型的公司都不享有的特权。
所以共和党人要想驯服这些科技巨头,真的需要摆脱这种心态。我想,这对共和党初选投票人来说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们关心这个问题,他们需要开始关注谁在资助他们的地方代表。不要因为他们名字旁边有一个红色的“R”(共和党),就认为你的代表会强力反对大科技公司。
解决方案:令公司开放过滤系统 过滤信息授权给用户
杨杰凯:让我们在这里谈一谈解决方案。很明显你描述了——这在书中有非常非常广泛的详细说明——你描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大公司已经实际上成为公共广场,但是它们是私人实体,并且目前在它们采取任何行动来控制言论方面几乎不用负责任。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对吗?当然230条款正在受到审视。我们知道,联邦通信委员会现在正在针对230条款制定新的规则。你认为接下来应该会怎样?
博卡哈利:我认为解决社交媒体审查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那就是直白地对这些公司说,如果你想获得这些你整个商业模式都依赖的法律特权,你必须给用户选择,让他们可以不接受你对合法、受宪法保护言论的所有过滤。
如果你想进行“仇恨言论”过滤或者“错误信息”过滤,可以; 但你需要证明,是用户选择开启该过滤程序。你不能代表他们切换到“开启”并禁止他们关闭。而这就是它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知道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例如推特和谷歌都允许用户关闭淫秽过滤程序。
但是你虽然可以关闭谷歌的“安全搜索”,但它们在涉及到“假新闻”或“错误信息”时就不给这个选择。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表明他们更关心的是控制政治信息、控制新闻的流动,而不是让消费者的选择最大化。所以这必须是对社交媒体整个行业的标准。
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特别是对搜寻引擎,强制实行透明和监督。我们需要能够看到幕后,看到这些算法到底是如何被训练出来的。我们需要看到能降低用户“品质分数”的东西。你的品质排名不能对用户隐瞒。这就是我要开的两个处方:第一,用户可选择退出所有的过滤程序,第二,更加透明。
杨杰凯:还有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前几天我们在Periscope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些算法是如何学习的内情,看看输入到这些算法中的哪些数据被用来代表仇恨言论,以及其它一些用于算法学习的问题。
博卡哈利:是的,算法其实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复杂。我在书中用几页的篇幅就解释了什么是算法。它们只是训练出来的。例如,“仇恨言论”算法,你训练它来识别“仇恨言论”。“硅谷认为什么是仇恨言论?什么它不认为是仇恨言论?”然后我们就会知道算法是否有偏见。
我们都能猜到它们忽略了什么样的东西。它们可能不会把“安提法”组织归类为“仇恨言论”。你给它提供了一堆数据、一堆例子说,“这是仇恨言论,那是仇恨言论,这不是仇恨言论”,然后你拿它去测试,你纠正它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不断改进它。所以对这样的算法进行某种监督的方法很简单:“好,我们应该能看到它用什么样的数据来学习。”
事实上,我和一位脸书的举报人谈过,他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不被允许把“安提法”归类为仇恨言论。他们被明确告知不能这样做。至少在2019年初,在他离开脸书之前,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审查算法的一种方式,看它们用于学习的数据。
杨杰凯: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怎么才能真正关闭所有的过滤程序?因为不管我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得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数据太多了,对吧——我们必须有一些系统来对它进行分类或者总结,让我们能够消化,增进用户体验。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合情理的。但它绝对是一种过滤,不是吗?
博卡哈利:当然是。我想很多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搜索结果或者推特上充斥着淫秽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推特和谷歌都会过滤掉这些内容。但即使如此,你仍然可以选择关闭过滤程序。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任何过滤。当然,我们不希望被淹没在口水战、骚扰等等。我只是说应该由用户来决定是否开启那些过滤。
对我来说,这些科技平台必须完全开放过滤系统。甚至应该允许第三方厂商制作自己的过滤程序并且可以插入谷歌或推特或脸书使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并将最大限度地增加消费者的选择。但科技公司永远不会主动这样做。因为如果它们那样做了,就等于交出它们所有的控制权、所有对政治信息和新闻的管治权。
杨杰凯: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的确是自由市场的解决方案。我想,它将实现过滤程序民主化,人们可以选择他们希望考虑的一家公司、一个个人的观点。否则,一些不知名的、可能扭曲“仇恨言论”的员工也许会决定这些事情。对吧?
博卡哈利:正是如此。这是我们需要瞄准的目标,也是人们应该敦促他们的代表对这些科技公司提出的要求。如我所说,科技公司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它们现在权力太大。它们非常乐于拥有这种权力。它们正在使用这种权力。我们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就看到了。而唯一剥夺这种权力的办法就是加强监管。我知道保守派对利用政府权力管制私营部门的想法感到畏惧。但我们要记住,在19世纪末,以这种行为最为闻名的总统就是共和党人泰迪∙罗斯福。
杨杰凯:阿卢姆,在我们结束之前,你有什么结语吗?
博卡哈利:我只想再强调一下这些科技公司对独立媒体、自由表达、自由公正的选举有多大的威胁,因为与学术界或主流媒体的偏见不同,这些公司不仅能够控制我们看到的信息,还能了解大量我们的个人信息。它们正在利用这些信息隐蔽地操纵我们的政治理念。我强烈鼓励大家去更多了解这一点以及这些科技公司的所作所为。你可以在deletedbook.com找到《#删帖》这本书。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将在中长期主导美国政治,你需要了解关于这些科技巨头的一切。
杨杰凯:博卡哈利,很高兴与你交谈。
博卡哈利:很高兴能来这里。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