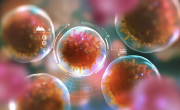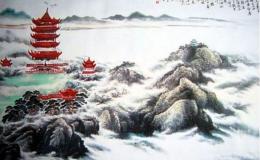每一颗扭紧的螺丝钉都有罪
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在加沙地带的武装冲突,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西方媒体上的讨论,左中右都有,这个要看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了。有一个可能比较右派的评论,我印象深刻,他说,二战期间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遭遇,是后来以色列复国的一个道德和法律基础。
犹太人二战期间在欧洲死了六百多万,大批犹太人在集中营中被虐待致死,战后真相逐步被揭露,震惊全球。后来,很多知识分子发誓“永不再发生”(Never Again)。
今天,我们不讨论以巴冲突,也不讨论国际政治冲突,我们谈目前仍然需要面对的同样的人道灾难。
前几天,北京法轮功学员许那,在海外发表了她的一篇文章,让我感受良多。许那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以前叫北京广播学院,她是一名画家,多次被抓进监狱,去年再被抓捕,再次入狱。
我先读一段她的文章。
“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关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不是中国的监狱。因为在纳粹的毒气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监狱,它让你活着生不如死。反复经历漫长的酷刑,酷刑中他们配备懂医的犯人看护,随时检测你的体征。我在那儿多日不被允许睡觉,被发现心律不齐。于是警察命令说:‘让她睡一小时,休息一下。’
各种各样隐蔽而精致的酷刑被发明,比如:劈叉,将双腿拉开成180度,命令三个犯人坐在受刑人的双腿及后背上,反复按压。警察自豪于这个发明:‘这个办法好,因为疼痛难忍,但又不伤及骨头。’
纳粹反人类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身体,而它们的目的是摧毁人的精神、良知。当我在酷刑与洗脑中更加挺直腰板时,一个警察认真地对我说:‘应该申请对你进行开颅手术,把你的大脑摘掉。’”
许那这段文字,让我们震惊吗?她宁愿自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那个我们发誓“Never Again”的地方。我们人类最大的恐惧,据说是生老病死,但死不是最可怕的,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
中共的监狱执行这种让人生不如死的政策,已经有七十年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不是第一批,也不会是最后一批。如果读一下法轮功学员的证词,就会知道,劈叉只是让人痛苦的其中一个方法,比劈叉更让人痛苦的刑罚,起码还有五六十种,每一个都可以导致人痛不欲生,也都令人发指。
纳粹的集中营,目标是消灭犹太人的肉体,中共的这些集中营,目标是消灭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你变成行尸走肉,变成奴隶。使人陷入无法忍受的痛苦,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
杀人很容易,改变人很困难,所以中共发明的让人痛不欲生的刑罚也就越来越多。
许那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时候正是大学生,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远离中共宣传部门和广电总局控制的那些机构,变成一个自由画家,希望能轻松度日。1995年,她和先生于宙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
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许那被抓关在监狱里面。
她在文章中说:“2003年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徐滔采访北京女子监狱,我被隔离在警察办公室。四个犯人,以人肉铐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听到不远处采访现场,对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讲它们如何文明执法,而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的嘴里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共同受教于以培养党的喉舌为宗旨的中国传媒大学,如今她是北京电视台的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
这次采访后不久,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监。最后称她为病死,我因检举、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实,再次被投入小号折磨。
几年后,同样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他为于宙的死做了伪证,但他说:‘我不敢讲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灭口。’”
许那的丈夫于宙,长得很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高瘦高。他是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生。
1999年8月,他们在北京房山参加了一次同修们的聚会。那次,来了几百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后来被中共非法判刑、现在在美国的博士生王斌(被中共劳教两次)、现在流亡海外的母亲刘桂芙,美国法轮功学员黄万青博士的弟弟黄雄(现仍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迫害发生后大家都想跟以前的同修见见面,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会后,于宙、许那夫妇为了照顾其他的同修,所以走晚了一些,被警察拦住,抓进看守所40多天。因为没抓住别人,所以警察们把他们俩口子当作聚会的‘组织者’严加审讯,可他们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同修的任何信息,他们在警察面前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勇、大仁、大义让警察都感到佩服,被释放后,地方片警不肯再为难他们。
2001年,曾经借住在许那家的东北四平法轮功学员李小丽(已被迫害致死)被抓,警察根据李小丽的电话号码,查到了许那另外租住的地方,7月3日北京市国安在通州绑架了许那。11月北京房山中级法院对许那非法判刑5年。
在北京女子监狱,许那受到各种虐待,仍然不屈服,后来监狱长周英批准,把许那关进“小号”折磨,2004年许那又被转入一个没有“法轮功”的劳动队,严管隔离。在监狱中,许那总是不断地向犯人们讲述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以自己的善心与正行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犯人和管教警察。时间长了,警察和犯人们都觉得许那说得好,说得对。因为担心许那把监狱里的人(从干警到犯人)都变成法轮功学员,监狱长经常给她调队,每次调队时,犯人们都洒泪与她送别。
2006年底,于宙的妻子许那被释放回家。夫妻也终于团聚了。许那继续在工艺美术界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回家后不久,就被中央美术学院看中,免试录取她读油画系的研究生。于宙为了保证妻子的学业,把家搬到校园附近。
几年后,同样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他为于宙的死做了伪证,但他说:‘我不敢讲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灭口。’”
许那的丈夫于宙,长得很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高瘦高。他是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生。
1999年8月,他们在北京房山参加了一次同修们的聚会。那次,来了几百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后来被中共非法判刑、现在在美国的博士生王斌(被中共劳教两次)、现在流亡海外的母亲刘桂芙,美国法轮功学员黄万青博士的弟弟黄雄(现仍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迫害发生后大家都想跟以前的同修见见面,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会后,于宙、许那夫妇为了照顾其他的同修,所以走晚了一些,被警察拦住,抓进看守所40多天。因为没抓住别人,所以警察们把他们俩口子当作聚会的‘组织者’严加审讯,可他们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同修的任何信息,他们在警察面前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勇、大仁、大义让警察都感到佩服,被释放后,地方片警不肯再为难他们。
2001年,曾经借住在许那家的东北四平法轮功学员李小丽(已被迫害致死)被抓,警察根据李小丽的电话号码,查到了许那另外租住的地方,7月3日北京市国安在通州绑架了许那。11月北京房山中级法院对许那非法判刑5年。
在北京女子监狱,许那受到各种虐待,仍然不屈服,后来监狱长周英批准,把许那关进“小号”折磨,2004年许那又被转入一个没有“法轮功”的劳动队,严管隔离。在监狱中,许那总是不断地向犯人们讲述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以自己的善心与正行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犯人和管教警察。时间长了,警察和犯人们都觉得许那说得好,说得对。因为担心许那把监狱里的人(从干警到犯人)都变成法轮功学员,监狱长经常给她调队,每次调队时,犯人们都洒泪与她送别。
2006年底,于宙的妻子许那被释放回家。夫妻也终于团聚了。许那继续在工艺美术界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回家后不久,就被中央美术学院看中,免试录取她读油画系的研究生。于宙为了保证妻子的学业,把家搬到校园附近。
一年之后,2008年1月底,于宙和许那的车被警察截停。那一年的夏天,北京会举办奥运会,中共全面加强保安。北京警察在他们的车上发现了一本书《转法轮》,所以把两人抓到警察局。
2月6日,于宙的父母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要求他们马上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当家属赶到那里,于宙已经停止了呼吸,尸体被用白单覆盖,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
于宙那时也在社会上漂泊,和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乐团,只有三个人,名叫“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小娟是一个残疾女孩,声音很好听,小强是她的男朋友,会弹吉他,于宙吹口琴,也打鼓,不是爵士乐的那种鼓,而是小型的民乐的那种小鼓。他们这个小乐团为乐迷们演唱各国的乡村歌曲,传统民谣,所到之处大受欢迎,拥有一群忠贞不贰的拥护者。小娟是个残疾人,行动不便,可在小强和于宙的帮助下,她顽强地在艺术道路上走着,渐渐的,她轻柔的歌声和乐观豁达的性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这个乐队小有名气,经常去各大酒店演出,2007年这个乐队进行了三次专场巡回演出,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晚霞》、《我的家》、《山谷里的居民》等深受歌迷喜爱,《我的家》成了每场演唱会的开场曲与谢幕曲。有公司还投资,专门为他们制作了一个MV。
2008年1月26日,于宙被抓之前,刚刚参加完一场演唱会。
十天之后,他死在通州看守所。2月7日,是中国新年的大年初一。乐队歌手小娟在她的个人博客中,发表了据说是多年前已经创作的一首歌曲,美丽的魂魄。这次,小娟用清唱的方式发表出来。歌词是这样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们会变成美丽的魂魄
飘在遥远的天空
也许是你先
也许是我先
折一朵天堂圣洁的玫瑰
在天堂静静地等候
家属询问于宙的死因,医生一会说“绝食”,一会说是“糖尿病”,而于宙身体健康,根本就没有糖尿病。而且人刚被关进看守所10天,怎么会因为“绝食”去世呢?为了掩盖罪行,中共的看守所逼迫家属马上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名义把于宙的家人“围起来”。于宙的家人坚决不同意火化于宙的尸体并要求尸检。看守所曾一度答应许那办理于宙的后事,可后来突然又说话不算了,还把许那转押到了北京看守所,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市局七处”,是北京警方专门处理所谓的“政治犯”和“重刑犯”的地方。
这是13年前发生的事情,当年11月,失去丈夫的许那被判刑3年。
去年7月,许那再次被捕,和她一起被捕的,还有多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罪名,是在疫情期间,在网上发表了几张街道上的照片。在中共看来,这几张北京老胡同的照片,严重威胁了中共的安全。
至今,许那还被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许那的母亲是美术学院的教师,已经去世,父亲是中国大陆知名画家,她本人的画作在中国大陆也颇有名气。
为她辩护的梁小军律师,在他推特中写道,“许那作为一个画家、自由撰稿人,她的学识、她自身的悲惨遭遇和坎坷命运,带给她一种深敛于内心的睿智、良知与勇气。”“残酷环境之下,她淡泊名利。她本应有的名气与影响,虽然被民间社会所低估,却为官方所不敢轻视。每次会见她,于我,都是一种聆听与学习的过程。”
许那对律师说,和她一起被捕的,大多是北京年轻的法轮功弟子,有些还不到20岁,所以她必须为他们战斗。她在最近海外发表的文章说:“这个世界每一件不公义,即使离你很远,也与你息息相关,因为他时刻拷问着你的良知。”
她说:有些事于我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我无可逃避。
所以她认为:“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这个机器的邪恶运转。”
面对那些罪恶假装看不到,甚至有意无意去配合的人,无论再无足轻重,在道德上可能都是有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此,今天也同样如此,这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文章转载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