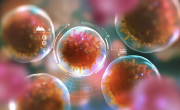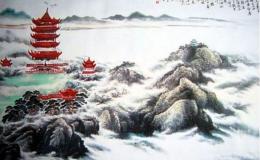共产集中营 20岁右派亲身体验到的虐待酷刑(上)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说中,使用“铁幕”一词准确地描述了当时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卫星国对其本国民众残酷如铁桶般的统治状况,从此“铁幕”一词便成为共产极权专制国家的代名词,且为世界所公认。然而在这“铁幕”的后面,还有更阴森黒暗的境地,那就是星罗棋布于共产专制国家里的形形色色的集中营:监狱、劳改队、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而其中对受刑人的种种虐待、折磨更令人发指,许多人更被活活地折磨致死。本人从不满20岁便在反右运动中,先划为“右派”又继以所谓“收听敌台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牢,长达二十余载。其中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的虐待、酷刑,至今还留在恶梦一般的记忆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因而对这些历史不能保持沉默。必须将其公诸于世,为历史作证,不能让那些作恶者的恶行不为人知。
酷刑曾惊动过毛泽东
在大陆的所谓监管场所(包括监狱、劳改队、劳教队、看守所、拘留所等)存在虐待囚犯(劳教队的所谓“劳教份子”其实就是变相的囚犯)和酷刑的问题,早已是“阿Q先生头上的疮疤——明摆着的”。此事甚至一度“惊驾”了“毛太祖”,毛还发过一道“最高指示”。那是1974年文革期中,我当时在四川省第四监狱刑满后被“强迫留队改造”称之为“就业员”。有天全狱召开“两类人员”大会。所谓“两类人员”即在押囚犯与就业人员的统称。大会由当时担任该监狱政委的王宗政先生作报告。平时不论大、小狱吏只要在会上口一张就叫“训话”或“作报告”,尔等“两类人员”不仅要洗耳恭听,凡有笔记能力者,必须秉笔恭录,否则,视为“反改造”行为。但那天会一开始,狱吏便宣布:“今天开会,由王政委作重要的传达报告,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只许你们规规矩矩地听,任何人不许作笔记,不许交头接耳,不许议论喧哗,违者按严重反改造行为论处!”一时气氛既紧张又神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
结果当天王宗政先生传达的所谓“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只有一句话,即“这些法西斯的审讯方法是谁发明的?必须立即废止”。前无头,后无尾,根本不知老毛所言何事。王宗政把这句“最高指示”念了两遍以后,便大谈了一通劳改政策如何伟大,对你们“两类人员”如何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好像毛说的不仅与我们这些“两类人员”毫无关系,甚至与中国都没什么关系,而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事一样。后来才知,原来是文革中一些“走资派”官员在被关押中遭到了酷刑,后来事情被捅到老毛那里。毛一时生气便写了这么一个“便条”式的“最高指示”。结果,上面放个屁,下面跑断气。便这么层层地传达了下来。但这也说明,这酷刑在中国之普遍与厉害。
不过“最高指示”传达以后,监狱里捆人,打人,依旧照捆,照打不误。血写的事实粉碎了墨写的文字。
虐待酷刑五花八门

我从1957年进四川叙永看守所起,酷刑与虐待就与我经常亲密的零距离接触。其品种,花样,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没有亲历过的善良的人们,是很难以想像得到的。可以大概分述如下:
一、最常见的是打人
对于囚犯来讲那简直是小事一桩。特别是狱吏不用器物,空手揍你一拳、一巴掌、踢一脚,根本不算一回事。四川省四监狱有个狱吏叫余继发,是共军一个排长“转业”,由于大字不识几个,只有调到劳改队来管犯人。他在四川泸州专区监狱时,有个外号叫“余一脚”。他经常穿着一双军用皮鞋,他看着谁不顺眼飞起就是一脚,故以得此“美名”。可能是踢人太多,后来一只脚患了骨结核,当时中国治疗结核病的水平很低,最后他那患肢比健肢短了近3公分,走起路来一拐一瘸,要想踢人便大有困难了。因而其“余一脚”的美名也被“余瘸子”取而代之。
但这个余瘸子脚不能踢人了,手打起人来照样够狠。一次,他用一根棍子打一个叫陈忠良的犯人,竟把棍子都打断了,陈被打得昏死过去。三年大饥荒时,我在芙蓉煤矿劳改,当时由于饥饿和缺乏营养,我患了夜盲症。那是因缺乏维生素A,眼的视网膜杆状细胞上无法合成一种叫“视紫红质”的物质,所以一到黄昏就看不见东西(民间俗称“鸡蒙眼”)。一天黄昏时中队指导员孙明清,叫我们几个囚犯出去给他搬什么东西。我向他“报告”说我看不见。他一听就火了,开口骂道:“你眼晴瞎了呀?叫你去吃东西,你怕比哪个都跑得快!”我说:“我得了夜盲症。”孙问我“啥子鸡巴叫夜盲症?”我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我话还未说完,“叭”一巴掌就打在我头上,“你狗日的反革命右派还敢污蔑政府,人民政府一天三顿给你吃得饱饱的,你还缺乏‘素’了,还要吃‘荤’不?……”边骂就给我一脚。那时的人虚弱得风都吹得倒,我一下就被他踢倒了。可他不但不罢休,反而一边乱骂我“装死狗”(四川方言,意即耍赖骗人),一边用脚在我身上乱踢乱踩,我开始痛得大叫,后来叫都叫不出来了,他似乎也打累了,才丢下我带着其他几个囚犯扬长而去。
1963年我在芙蓉煤矿5中队种蔬菜,一个姓宋的分队长,说我挑粪的粪桶没有装满,是“偷奸耍滑磨洋工”,于是他折断一根树条劈头盖脑就给我打来,而且就像鞭打驱使牛马牲畜一样,边打边吼“给老子快点走,快点走!”当天中午还不许我吃饭。在这个宋狱吏的眼中,我们连牛马也不如,牛马干了活,也要给草料吃呀。在这个矿的张家村菜蔬中队,有个狱吏叫甘大全,外号人称“甘扁担”。因为他一天到晚手上就握着一条扁担,不是为了挑抬东西,而是他打人的工具。我亲眼看见一个姓王的囚犯,因为到菜地里偷生豌豆吃,被他看见了,冲上去一扁担就把那姓王的肩关节打脱了臼。
二、支使犯人打犯人 虐待犯人
在当年的劳改政策中,也有不许打骂,虐待犯人之类的仁义道德的词语,不过那大半是拿去糊弄“洋鬼子”的。就像今天我们神圣的宪法里还明文写着,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咧,你去“集”个会,或“结”个社来看看,看那警察局敢不敢欢迎你去“作客”?我在劳改队几十年,狱吏们惯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不打人、不骂人。我们不打、不骂接受改造的”,言下之意,你不接受改造,你反改造,不打你,打谁?至于什么是“接受改造”,什么又是“反改造”那是由狱吏的两张嘴皮来“决定”的。于是有些聪明的狱吏,为了保险和省事,干脆就纵容、甚至支使犯人,去打犯人和虐待犯人。这样一来,狱吏便更加“超然”和主动了。万一出了什么乱子,就像今天的“躲猫猫”一样往“牢头、狱霸”身上一推,便万事大吉。而一些想“积极接受改造,想争取立功减刑”的犯人,也积极、主动与狱吏配合。有的甚至“变态”到了以此为乐,乐此不疲的状态。特别在批斗“反改造”或逃跑犯的斗争会上,有的是为了表现积极,有的是为了报平日鸡毛蒜皮,睚眦之怨的私仇,有的甚至就是去发泄、取乐。反正在狱吏的纵容下便都去对被批斗者打骂折磨。反正打了人还被“党和人民政府”肯定为“积极接受改造的好表现”,天下有比这更占便宜的事吗?
文革中我在四川省第四监狱,看见斗争一个完全是精神分裂症的囚犯叫李丁,他说他对马列主义有“独到的发现”,还要“和毛泽东同志商榷”。稍有判断能力的人听了都知道是个疯子,但当时就硬说他是“反动透顶”,恶毒“诬蔑领袖”。于是弄来斗争,罚跪,拳打脚踢。有天晚上我看见我们的一位右派难友,左一下、右一下的在李丁脸上“左右开弓”地打了不下十个耳光,对疯子也这样无情地折磨。而这位老兄前几年还在写文回忆李丁。
犯人中,还有“特殊犯人”。我在芙蓉煤矿张家村队时,有个囚犯叫梅亭秀,名字像个女子实则是个男人。是原古叙农场劳改队的干部。1957年划成右派后,又在其日记里发现有“反动言论”,于是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到了芙蓉煤矿后好多狱吏都是他认识的熟人。起码对他比较放心,于是让他当“犯人大组长”,每天不干体力劳动,哪些犯人干什么活,则由他来具体分配。更不得了的是他有权决定你每天伙食的粮食定量标准,是甲、乙、还是丙等。当时多一口粮食就是多一点生的希望。所以梅大组长,犯人背后都叫他为“二管教”。这梅二管教,每天是东走走,西看看,看见那个干活不卖力,他就可以打你两下子,所以没有哪个犯人不怕他。更奇怪的是这个牢头狱霸,劳改还不到五年,便被改判释放。劳改队的所谓“大组长”、“学习组长”之类的“犯人官”,往往都有过去曾是什么书记、党员之类的背景,才有资格成为狱吏“以犯治犯”的工具。
而现在听说好像“风水”有点“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了。现在监狱中的犯人如家中亲属是当官的,大企业主有钱的,则特别受“优待”。上世纪九十年代,四川省第四监狱监狱长冷待发先生(后因腐败被判刑),他就敢把犯人叫来对他说“我知道你家里有钱,叫你家里给监狱捐一万元,可以给你减一年刑。”那时的一万元,不比现在,民间“万元户”就是富翁了。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 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