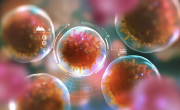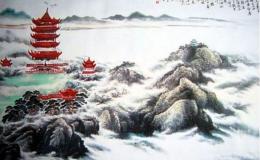后悔加入中共 翻译家杨宪益愤然退党
也不知有多少人后悔“走上革命道路”(下)

其实,不只是在1949年后,即使中共获得政权前,就已经有无数革命者后悔走上这个道路,而且有人当年就已控诉。尽管在其他回忆录中我们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的现象,可韦君宜的《思痛录》毕竟是她个人经历,这样,就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中共历史是怎样一种“丰富”的“革命历程”。
《思痛录》中有一章题目叫《“抢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读来,读者也能感受到当年的惨烈: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有一时间段,仿佛延安到处是“特务”。
韦君宜女儿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回忆:“父母告诉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当时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甚至明知被审讯者不是“特务”,审讯者也会编造口供送上去。大约也正是这种荒谬之极的现象,让一些天真纯洁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别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后悔不已。
有一个叫吴英的,是从天津跟韦君宜一起出来干革命,在延安见到韦君宜后,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说着说着,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17页)这让韦君宜感到很难堪,“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以对”。
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韦君宜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然说道:“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17页)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她绝没有如此说话的勇气。当时一定是豁出去了。

韦君宜说她当时听了这个叫丁汾的讲的这些话,使她胆战心惊,如冷水浇头,“我倒是不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作者气的是中共当时“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18页)作者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如果这个叫丁汾的女革命者能活到文革,如果人们又知道她当年曾说过那样几句话,即使不死,也要脱层皮。
当自己读到这些,就在想,“早知今日”,也不知有多少人不会背叛自己的家庭,更不会加入中共不会“奔赴延安”,而没有这众多热血青年的加入,中共是否还能取得最后胜利获取政权,可就是未知数了。特别是从书中记述来看,那些年早就把人心搞乱搞坏了,而且1949年后非但没有真正“收拾人心”,反而一直把人心往邪路上引,这才是这个国家至今还在这个邪恶的社会里打转转的缘故。
作者之所以将书取名为《思痛录》,想来,正说明作者的痛,钻心的痛。而通读增订版,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看到作者的痛里包含着后悔,深深地后悔。
在说韦君宜的“后悔”之前,不能不提到韦君宜的丈夫,可以说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事实上到死都不能算是一个觉悟者……
现在想想,这个组织不就是在一大群像杨述这种所谓“有坚定信仰”的人维系着一直走到今天的吗?如果反右派运动或是文革之后,跟着中共“闹革命”的人都觉悟了,至少都像韦君宜这样觉悟了,这个组织还能支撑到现在吗?
作者怎么也没想到,熬到有自己参加的中共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获得政权后,这些革命者包括对中共作出巨大贡献的傅作义的女儿以及陈布雷的女儿仍不得安生,仍然让她们感到痛苦不堪,甚至痛不欲生。大约也像那个叫丁汾的女孩子一样,当这种痛苦不堪到极点时,是难免要流露甚至要发泄的。
反右派运动让韦君宜再一次感到困惑,后悔之情溢于言表。在反右派运动中,韦君宜曾对黄秋耘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特别是当她看到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极其丑陋的人和事,她“心里的痛苦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这几句话足以表明韦君宜对参加中共革命的后悔,对中共政权的失望。韦君宜不就是又一个吴英又一个丁汾吗?她所说的这些话,与当年吴英和丁汾所讲的那些话难道不是一个意思吗?如果真要说有差别,也只是前面两位说那些话是在中共取得政权前,而韦君宜是在中共获得政权后。想一想,在中共内部,连是否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也需要选择,这让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很难理解。
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他“其实是一个上层富家子弟,却充满了叛逆的性格,真心向往革命。……他从事秘密的反蒋活动,向中共提供情报,还曾经要求去延安,但是未能成行。1949年以后,他热情地拥护新政权”(引自《他们不可能摧毁所有的高贵——翻译家杨宪益礼赞》)。杨宪益娶了一位同样有学识的英国姑娘戴乃迭(戴乃迭是她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字: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共刚获得政权时让其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书。夫妇俩都是那么相信中共所宣传的东西,尤其是杨宪益的妻子,无论英国的父母亲戚怎么劝她不要过分相信中共那一套,她非但不听,还总是表达自己“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尊敬”,并为“外国人民不明了中国的真实情况”“颇为遗憾”,拒绝英国父母亲戚给她寄路费或生活用品。她“当时觉得总没有什么任何组织比国民党更坏;因此当我家里人写信来问我是否需要路费以便回国的时候,我谢绝了”。她在英国的父亲来信认为她不过是在“替共产党宣传”,甚至告诫她“也许有一天”会因此“感觉懊悔”;而她在英国的“有些亲戚”也写信问她“是否吃得饱,并表示可以给她邮寄食品等”(参见201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戴乃迭短文两则》)。
戴乃迭去世后,杨的妹妹还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要替祖国对她的嫂子说一声:谢谢!因为她的嫂子即使在文革中被关进牢里,每餐接过窝头菜汤,都不忘说一声:谢谢!而杨宪益,也是一再相信中共,直到发生八九六四,愤然退党。
有人采访周有光时,他说了下面几句话,现在就容本人以这几句话结束这篇用史实串成的文章,证明即使像杨宪益这种“坚定的信仰者”,最终也还是不能不对自己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打心眼里后悔,并且是那么决绝:“……他青年就倾向共产主义运动,所以他后来早期就参加共产党,到后来他的意见也不对了,变成反革命,开除出党。后来又改变了,四人帮打倒之后,后来又入党,到最后他又脱党。他也是‘两头真’,他的波浪比我们更大。”
需要补一句的是,这里周有光说的是“脱党”,而我在彭小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这篇长文中看到说的是:“杨宪益在六四后愤然退党”。我想,“脱党”和“愤然退党”,在词意上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吧。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