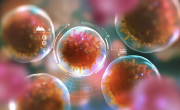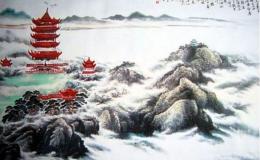代价惨烈:知青一代的苦难 我无法忘怀

我同班同学,小学是大队长,在全北京市小学生征文赛中得过第一名,中学一上学就被封为班长,右派家庭,文革中倍受歧视,落落寡欢,六八年自动提前报名去了内蒙插队,在乡下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认同,竟然放火烧麦堆,然后再奋勇救火被烧伤,被大队表扬,不几天,公社武装部来人,据说查出此火是他所点燃,于是锒铛入狱。这场革命把一个青少年逼到绝路上去,因为出身不好,又不甘心无法见容于社会,真正成了“引火自焚”。他的经历是极端的,却是真实的,数年后消息传到学校同学处时,我怀疑他的精神是否还健全,怎么能干出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实在无法把这样疯狂举动和一个老实斯文上进正派的印象联系在一起。
七八年春天,他突然到我的大学校园找我,原来刚出狱不久,我和他坐在学院大树下,众目睽睽,聊了四个小时,害得同学以为他是我的追求者之一,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们躲在远处议论得哈哈大笑,男女生不时探头探脑,佯装路过(后来女生透露给我的)。等我讲了他的坐牢遭遇,很有几个人掉下眼泪,再也不笑话他的未老先衰的相貌和早早花白的头发了,因为我的班上,也有很多鲤鱼跳龙门一样历尽艰辛才考上大学的老三届,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告诉我他的右派父亲文革刚开始自杀身亡,母亲病倒,大哥被打成反革命,随后也自杀了。上小学的妹妹成了神经病,他在学校无人理睬,在家没饭吃,不得不自寻出路,去内蒙古比别处容易,离家近一点,还能维生,而且他想用自己积极的表现改变前途。他的眼睛深度近视,神情颓唐,瘦弱不堪,一个是前途在望的七七级英语系学生,一个是刑满释放无业无户口的内蒙知青,我不知如何来安慰和劝解他,唏嘘无言,再多的话也是惨白无力的,想起在六四年秋天入学时,他是文质彬彬的三道杠大队长,受同学尊敬的班长,此刻“落魄江湖”,“我见犹怜”,对不起,这应该用在男人对好看女孩“怜香惜玉”时的用语,可我却没有其他语言来形容当时见到他的感受。
他要我读一下他写的小说初稿,准备投去发表,那时正是清除四人帮罪恶,平反拨乱之际,《人民日报》对文革的定义是“十年浩劫,天怨人怒。”他对毛泽东的总结是“恩比天高,罪比海深。”我一听大吃一惊,极力劝他不要再为自己找麻烦。当时我有一种成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对邓小平的政策充满感激之情,对打倒四人帮后的形势充满乐观,高度的理想主义情操又注满心怀,我苦心地劝他一定要把才能放在知识学问上,争取考下一届大学,至少要争取用自己的努力学习一门技艺来谋生,别用耸人听闻的词语来博出位,甚至出于同窗之谊,用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来规劝他。
他非常失望,他讲为什么他敢把心里的话告诉我,是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原来六五年小学考中学的作文,叫做“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我们六四年入学,已经是初一的孩子了,老师也让我们做这篇作文,改为“我的家庭——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班上有几个同学得了五分,包括我在内,几篇范文贴在墙上。有革命子弟的,也有一般子女的,也有他的和另一个全班男女生都最崇拜的另一个男孩的作文。
没想到他俩写出自己石破天惊的家史,一个父亲是右派,一个父亲自杀了。那位父亲自杀时还在襁褓的同学,是国家队即将选走的少年运动员,从小似乎一直在阳光下生活,只是刚刚被组织告之这一消息,他才知道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只是继父,并被鼓励不要背家庭包袱,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在等着他,因为他获得了全国少年游泳冠军,他将是要为国家争光的金牌选手等等等等。
我们住校女生当晚被这两篇作文感动的热泪盈眶,觉得不必为另一位锦上添花,他已经是国家栋梁了。(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体育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肯定与家庭有关)我们都可怜这位班长有这样的苦难和认识,他写到他的心里充满自卑,别人都在阳光下,小小年级他却在巨大的家庭阴影下,不敢说出心中感受,只能拚命读书,来到这样的学校既感到荣幸又感到悲哀,他永远也不会入团,也许都不能上大学,他的哥哥功课全校第一还是考不上大学,怎样他才能让别人相信他也是红色少年,是跟党走的,怎样他才能脱离家庭的影响,他愿意作脱胎换骨的改造……
大家觉得应该写一封革命的信来安慰和鼓励他,于是几位女生连夜口述和商量,我成了主笔,写出一篇“感动”自己“感动”他人的信,第二天全班男女生都签了名,无非是抄袭了当时最时髦的语言,“出身不能选择,重在表现,作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都是你的阶级弟兄姐妹……”之类废话,没想到感动得他热泪纷飞,在人生最低谷时,他想起了我们几个好心的同学,并辗转找到我的学校,只想叙叙心声。
文革开始,家庭出身成了他的罪恶,我也被同学批评成“小资温情、划不请阶级路线……”加上学校高干子弟众多,自来红一片一片,我基本上自身难保,是一个几乎要被划出的“修正主义苗子,学校树立的白专典型”。又是我老爸推迟出生几年的选择救了我,他四八年刚从大学毕业,兵荒马乱没找工作,定为职员,我才能当个不红不黑不温不火的逍遥派,反正整不着我,成为奈何我不得的女红卫兵的眼中钉,学校老师校长心中的好少年。
如果假设有或没有以下的几个不小心,我的命运就会大不一样了。一个不小心我爸爸要养家糊口而为旧政府工作了一年;我爷爷十岁离开安徽皖南乡村去南京投奔他当南京商会会长的堂哥而勤劳发迹,一个不小心日本人烧了我爷爷南京的房产店铺而促使他拖妻带子跑到乡下避难促使奶奶变成佛教徒,一个不小心爷爷奶奶想到财产会毁灭而教育跟随终身,就供五个儿女上了中国的名牌大学,一个不小心我爷爷没把土地捐给他乡下的祠堂而变成开明地主,那我们的成分就会改变,我们家就得遭罪了。毛泽东一句语录“开明地主,还是开明士绅”可就救了我家两代人。尽管我自己和家庭没有受到最直接的政治影响,但我看到听到感受到的却深深加强了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也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充满将心比心的情感。
说到我们的讨论,我不同意他这样想,而且认为他太灰,要激励自己,跟上社会,忘记过去,我把心中的全部同情都给他讲出,力劝他别招惹政治是非,刚刚二十六七岁,我告诉他我为什么选学外语,就是为了躲开政治,给自己一点自由天地,数理化学不了,政治是空头的,中文不能碰,历史也和政治关联,我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写东西是危险的,不是我们应当作的。
他还是对我失望,认为我不是六五年的曹小莉了,那时多么地纯洁,多么地正义,现在变得软弱,失去锋芒,我真是哭笑不得,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当年也是人云亦云,懂得什么?“早岁哪知世事艰”,现在经过十二年的煎熬,想的就是如何弥补失去的青春,那有功夫去算别的帐,我根本不想去沾惹政治是非。现在想起来我这位同学对社会的认知肯定比同代人深刻,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余生还在付着惨烈的代价,因为他是刑满出狱犯,就如同强奸未遂犯、摘帽右派,没有土地、农村最穷最底层的人是地主成分一样地荒诞,经不起世界法律推敲,可是给了中国法律不给他正常公民待遇的理由。
我在一九九六年阔别十二年故乡后回京时,遇上全班同学,这是自上山下乡后全班藉欢迎我的机会第一次聚会,除了我一人正式上大学外,还有几个工农兵大学生(万里表妹,妈妈是万丹如——全国最高法院院长,以及两三个高干和工人子女),几个后来上夜校的,几乎全军覆没,境况都不好,如没有文革失学,我敢担保百分之百能上大学。百分九十以上的同学是各个小学大队长、中队长,品学兼优,百里挑一考来的。
这位同学没联系到,在我要上飞机场的那天出发前,他打来电话说刚刚知道,非要来送行,但是来不及了,他的境遇仍是全班最差的,九十年代中四十多岁还没结婚。前几年听说他五十多岁时勉强娶了一个残疾人,抱上了孩子,穷得在北京待不下去,去一个小县城生活了。这也是一位知青的遭遇,经常想起就很痛心,他的资质极高,长相也不差,在牢狱里没死就算万幸。
一九九六年至今,我苦难的知青一代经历,为什么总是无法忘怀?
文章转载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