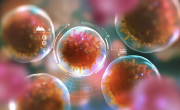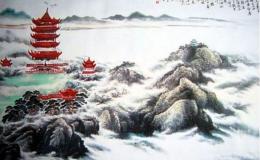自由开放的科学讨论遭大科企封杀
希尔斯代尔学院科学与自由学院的创始研究员马丁•库尔多夫博士、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杰伊•巴塔查里亚博士谈科学审查。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医生和专家们告诉我,他们看到自由和开放的科学讨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并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今天和明天,我将参加在华盛顿DC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柯比中心举行的关于科学审查的会议。
今晚,你将看到会议的公开部分,我们将听取我之前在节目中采访过的三位重要的思想领袖的发言,他们是前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马丁•库尔多夫博士(Martin Kulldorff)、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博士(Jay Bhattacharya),以及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Dr. Scott Atlas)。这三人都是希尔斯代尔学院科学与自由学院的创始研究员。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思想的自由交流受威胁 因此创建科学与自由学院
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正如我们所知,这场大流行病及其管理已经暴露出许多感染以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科学的政治化。科学程序已被破坏,而思想的自由交流,坦率地说,在美国受到威胁。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我们需要做的不应只是对它感到焦虑。因此,阿恩博士(Dr. Arnn)凭借他的智慧发起成立了这个新的科学与自由学院。
我是斯科特•阿特拉斯,与我的同事马丁•库尔多夫和杰伊•巴塔查里亚一道,都是联合创始研究员之一,我相信在座各位也都认识他们。很荣幸能与在座各位一起工作,成为一个团体。今晚我特别高兴地介绍马丁•库尔多夫,作为我们的演讲嘉宾。
他是一个原本不需要介绍的人,但是我很荣幸地介绍一下。马丁是哈佛医学院的医学教授,十多年来,他是疾病传播与监测的统计分析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之一。他曾是CDC(疾控中心)和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顾问和某些委员会的成员,曾为纽约市健康和心理卫生局提供帮助,还曾担任FDA的药物安全和风险管理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马丁开发了用于疾病监测的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方法,以及用于指示疾病爆的早期检测以及药物和疫苗安全监测的新型统计分析方法,这在如今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马丁开发了统计分析方法,今天在CDC和纽约市等地以及其它卫生部门用于监测COVID-19。
他的确是一个我们认为他可能知道的所有这些领域的权威,但是他的能力不止于此。马丁确实是我在这次大流行中,我几乎可以说,“在这场惨败中”,认识的所有同事中最有勇气的人之一。人们可能还记得,我受到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一群教授的谴责,而马丁•库尔多夫是全国唯一有胆量公开给斯坦福大学写信的科学家,不仅为我所说的话辩护,还特别向所有签名者挑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不用说,没有人接受这个挑战,去与马丁•库尔多夫辩论。因此,我非常高兴、荣幸地介绍马丁,作为这个新研究所的同事,作为一个勇敢和诚实的人,作为一个朋友。马丁,请。
马丁•库尔多夫博士:谢谢你,斯科特,谢谢科比中心和希尔斯代尔学院今天接待我们,也谢谢科学与自由学院的这项倡议。我认为科学已经崩溃,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机构,来长期帮助拯救科学。我确实找到了很多统计和流行病学的方法,但是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我今天不打算向你们展示一个数学公式。
武汉疫情爆发 研究发现老年人有风险 但发不出去
相反,我打算谈谈科学中的审查问题,就算是一个个人经历吧。当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时,你必须意识到还有其他科学家,他们受到的审查比我更严厉,但我将告诉你们我的故事。然后,你可以想像一下其他人是如何经历类似情况的。
如果你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两年前,在2020年3月,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武汉爆发了这种新型疾病的消息时,我感到非常害怕,有大约20分钟的时间,因为这种大流行已经进入了意大利和伊朗,这是中国以外最早感染它的两个国家,我意识到,我们都将感染它,它将会传播到整个世界。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阻止它。它的传染性如此强大,它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传播。这是非常清楚的。
当然了,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像所有父母一样,我更关心我的孩子,而不是我自己。所以,我想知道,他们有风险吗?所以,我查看了武汉的数据,那是当时唯一可用的完好数据,我看到了这个风险因素。当然,任何人都可能得这种疾病,被感染,但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差异超过一千倍。
我想,“嗯,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它实际上决定了我们应该使用什么策略来治疗这种疾病。”我不再担心我的孩子了。他们会安然无恙。我算是中间段年龄那一组。当然,对于老年人,我们应该非常关心,要确保他们得到保护。
但是,我试图发布这种简单的计算,却很困难。我在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我只有20年的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的经验。也许需要有30或40年的经验才能让人信服,我不确定。或者,也许是因为我是哈佛大学唯一一个这么说的教授,也许他们想要一个更有声望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办不到。
最终,我把我写的东西贴在了LinkedIn上面,因为经过三到四个星期的尝试后,我可以在那里发布任何我想发布的东西,因为我想,“好吧,没人想听这个。”但这实际上很重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当时已经有人知道这些情形,知道什么是保护老人的合适方法,但为了孩子又不能关闭社会,等等。
所以,我把它贴在那里,只是作为一个历史文献。我是瑞典人,我在阅读瑞典的应对方法,是有点不同的。但我有点担心,因为在瑞典有一场辩论,所以,我有点担心那里的公共卫生当局——例如,他们没有关闭学校——我担心他们可能会在压力下屈服。
所以,我决定,“好吧,我应该用瑞典语写。”因此,我在两家主要的日报上发表了三篇专栏文章。在瑞典发表这类文章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好吧,如果瑞典能坚持到夏天,那么每个人都会看到那是正确的方法。然后,每个人都会遵循瑞典的做法。很好。”伙计,我想错了吗?
后来,我还在英国的一个不知名的在线杂志上发表了它的英文版本。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追溯,当时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很难,这有点儿令人沮丧。我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办法。实际上,我设法让CNN发表文章。我为CNN西班牙语版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因为我知道如何写西班牙语。英文版,即CNN英语版,不想登它。
但我那么尝试了。但我们在努力,想着,“我们如何能够教育记者?”或者,“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个信息传出去?”还有,斯科特非常勇敢,仗义执言,但他们总是解雇他:“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说),他是一个放射学家,等等……”其他人也被解雇了,因为他们是在孤军奋战,或者他们不是……他们总是被描绘为有问题的人,于是大家都沉默不语。
起草《大巴灵顿宣言》聚焦老年人风险 遭强烈攻击
于是,我们想,好吧,我们三个人,我和杰伊•巴塔查里亚博士,他坐在这儿的后面,还有苏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博士,在我看来,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传染病技术专家,我们聚在一起,起草了《大巴灵顿宣言》,只有一页纸。我们主张更好地聚焦于保护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同时让儿童和年轻人过上接近正常的生活,以尽量减少这些封锁和其它措施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附带损害。
好吧,宣言引起了一些关注,也受到了强烈攻击。每次我读到关于它的文章,不管是什么报纸,为了攻击它的,上面总会有《宣言》的链接。我说,“好啊”,因为这样至少有一些读者会真正点击宣言,真正阅读它。到现在为止,我想大约有93.5万人签署了这份宣言,这让我们非常欣慰和感激。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的反应是写信给托尼,也就是福奇博士,说“看看这三位边缘流行病学家的提议。”今天在座的就有其中两位“边缘流行病学家”,“他们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见了面,似乎得到了关注。”
“需要对其前提进行快速和毁灭性的公开否定,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它正在进行中吗?”你们知道福奇博士是怎么回答的?“我在下面黏贴了《连线》(Wired)杂志的一篇文章,它驳斥了这一理论。”我相信这位记者可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但是福奇博士把他作为流行病学的权威,这有点令人吃惊。他是一个通常为《连线》杂志报导气候、食品和生物多样性的记者,也许他比福奇博士知道得更多。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但是……
这是几天后的另一封邮件,也是来自福奇博士。他认为,我们与几十年前那些否认艾滋病的人相似,这有点奇怪,因为《大巴灵顿宣言》的目的是主张更好地重点保护那些最高风险的人。这是它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我们不相信COVID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我不太明白这个逻辑,但是这确实是他写的。
出现有组织的运动反对《大巴灵顿宣言》
于是,出现了一种有组织的运动反对《大巴灵顿宣言》,有各种奇怪的指责,说它撒谎,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被想像成是在搞驱魔、搞优生学,是小丑、反免疫者,谋取经济收益,尽管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被指责为威胁他人,而我们谁都没有这样做。我们被当作是川普分子、自由主义者和科赫资助的伪科学家,说我们在写《大巴灵顿宣言》时得到了一份免费午餐。其中有一条其实是真的。实际上,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免费午餐。实际上,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两顿免费午餐,味道不错,是很好的食物,除此之外,是的。
那么,本次演讲的重点是审查,包括直接审查和其它形式的审查。因此,当《大巴灵顿宣言》发表时,最开始它出现在谷歌搜索引擎的顶部,但后来突然就不见了。相反,那里出现了一些批评它的人。其它搜索引擎把它放在顶部,但谷歌没有,对此有一些讨论。然后,过了一星期左右它又出现了。我想……但是谷歌一直否认他们做了什么。CDC、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LinkedIn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被审查的内容。
2021年4月,我在CDC的一个委员会任职,一个负责COVID疫苗安全的工作小组。有一次CDC决定暂停强生公司的疫苗,因为有一些血栓的问题,这些血栓发生在5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身上,但他们决定暂停所有年龄组的疫苗。从数据上看,这是非常清楚的。
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如何尽可能快地发现是否有不良反应的问题,使用后继分析,而不是每周看数据。我非常清楚,对于50岁以下的妇女来说有一个担忧,但是绝对没有证据。实际上有证据表明,50岁以上的人无需担忧,而这些人才是真正需要这些疫苗的人。目的不是为了年轻女性甚至是年轻男性,他们不是这种疫苗的主要受益者。
强生公司的疫苗很重要,因为它是单剂量的。因此,它有利于接触到难以接触到的人,如农村地区的人,或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很难得到第二剂。这一点很重要……在我决定要……以后,他们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大感兴趣。
反对暂停为老年人接种疫苗 被除名 遭大科企审查
所以,我在《国会山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暂停为老年人接种这种疫苗。然后,他们把我从委员会中除名。四天后,他们取消了暂停。但后来,损害已经造成,因为它已经得到了一个坏名声,甚至……这是在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期。所以,在那些没有得到它的人中,有一些人死了。所以,我猜想,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因为过于支持疫苗而被CDC解雇的人。
也是在2020年春天,我在Twitter上发文。有人问,“你认为年轻人应该接种疫苗吗?现在,那些已经感染过COVID的人该怎么办?”我说,“不,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接种疫苗,如同认为没人应该接种一样,在科学上都是有缺陷的;COVID疫苗对年龄较大、风险较高的人和他们的看护人很重要,而对那些先前自然感染过的人或儿童不重要。”
对我来说,这只是基本的流行病学常识,没什么奇怪的。但是Twitter上有一些人,我猜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不喜欢它,于是他们审查了它,所以没有人可以分享它或回复它,或喜欢它,这基本上意味着几乎没有人会发现它。
后来,他们把我排除在外面,我想大约三周左右,因为我在Twitter上发了关于口罩令的帖子,说“由于声称口罩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一些老年人会相信,他们会去办事,并被感染,以为它能保护,但其实不能保护。这不太好,因此,他们可能死于关于口罩的错误信息。”我猜这让Twitter……三个星期以来,因为这条Twitter,我无法访问Twitter。
还有另一件事,布朗斯通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罗伯托•斯特朗曼(Roberto Strongman),他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从事黑人研究的副教授。他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历史专业文章,说明口罩在历史上是如何被使用的,例如,用来压制奴隶的声音。他谈到了阿纳斯塔西娅(Anastacia),她是巴西的一个圣徒,曾经当过奴隶。这在Twitter上也不受欢迎,所以也被审查了。
Facebook把《大巴灵顿宣言》的页面关闭了一个星期,没有任何解释。说它是由问题的帖子,因为我们认为,对于当时刚刚问世的疫苗,我们应该优先给年长的、高风险的人接种。这就是导致Facebook关闭它的原因。有些人对关闭提出抗议,因此他们在一周后又把它恢复了。这是Facebook的审查。
YouTube方面,4月份我们与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包括我和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杰伊•巴塔查里亚博士和苏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博士。我们谈论了儿童不需要戴口罩的事实。我们还反对疫苗护照,当时关于疫苗护照的争论已经开始。所以,我们想,“我们得从一开始就反对它,在它起动之前。”于是就被谷歌下属的YouTube删除了。
LinkedIn隶属于微软,也在进行审查。所以,有一篇文章……是我在《大纪元时报》所做的一篇采访,内容是关于疫苗强制令的危险性。现在,他们稍微好一点,我想,因为他们“只让作者一人看到这个帖子”,因此,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帖子,但其他人不能。所以,至少,他们没有把它从我这里删除,所以那是……是的,这是另一种情况。其实我什么都没写,只是转发了一个来自冰岛的人的LinkedIn帖子,他所做的只是引用了冰岛首席流行病学家说的话,他有点相当于美国的CDC主任,因此代表的是冰岛官方的公共卫生机构,但还是遭到了审查。
这是另一篇,在这里他们更严厉一些,因为连我都不被允许阅读这条推文,他们完全删除了它,因为我当时提出,从COVID中康复的人是拥有最佳免疫力的人,比那些接种疫苗的人更好,所以是最不可能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因此,医院应该雇用这样的护士或这样的医生,用他们来照顾老年病房或重症监护室里最虚弱、年龄最大的病人,因为他们最不可能感染这些病人。
相反,医院在开除他们。LinkedIn不喜欢这个帖子。还有一例,我们和巴塔查里亚博士一起写了一篇文章给《新闻周刊》,讲述了福奇如何利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愚弄美国,LinkedIn也把它删除了,但是微软新闻重新发表了它。
微软的一个部门正在审查这篇文章,因为LinkedIn为微软所有,但是微软的另一部分实际上正在重新发布它,因此,我想,我不应该对微软过于不满,但是有点……所以,也许他们只是有点像是审查自己,或者做类似的事情。
这里还有一篇文章,微软或LinkedIn不喜欢,因为我提到,“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我们指责病人,污蔑同性恋,我们进行恐惧宣传,我们忽视穷人,治疗缓慢,而且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是由你知道的人领导,而在COVID大流行期间,我们仍然指责病人,污名化未接种疫苗的人,制造恐惧,而且封锁对穷人的伤害最大,治疗缓慢,而且NIAID是由你知道的人领导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汲取教训呢?”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汲取教训。
后来,LinkedIn实际上关闭了我的账户。布朗斯通的杰弗里•塔克(Jeffrey Tucker)随后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在Twitter上发表。所以,我从未要求恢复,但他们自动恢复了。所以,我想,是LinkedIn的某人读到了杰弗里写的东西,算是推翻了决定。所以,这是我在被叫停前的最后一个帖子,我说“通过解雇从COVID恢复后有了自然免疫力的员工,医院赶走了那些最不可能感染他人的人。”我认为这有点像轶闻性的事实,正是那条推文让我陷入困境。
遭大科企集体封杀 无奈开始“自我审查”
因此,Twitter、LinkedIn、YouTube、Facebook,他们已经永久性地叫停了许多账户,包括一些科学家的账户。我一直继续发声,但自那以后我就自我审查了,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交流渠道,所以我不想被删除。所以,我对我所说的话很小心。有一段时间我在想,“好吧,我真的不想这样做,因为我应该能够说出我想要说的东西,也许我应该忘记Twitter和LinkedIn。”
我和我的一位要好的朋友谈了谈,她也在哈佛大学任教。她的家庭来自斯洛伐克,她的家庭非常积极地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权。她的祖父是那里的主要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她告诉我说,“不,不,不,不,你不能就这么走开,你必须使用他们允许你使用的任何东西,然后,你必须注意你能走多远,以便能够继续做下去,否则,你就让他们赢了。”所以,她说服了我,“好吧,我需要继续利用这些场所发声。”
但是审查导致了自我审查,拒绝自我审查的人就会成为受害者,因为他们看到别人被审查了就会想,“好吧,我不想被叫停,所以,我说话最好要小心。”当然,这就是专制者的目的,也是这些事情的目的。有时,他们像是在那里随机选择他们要审查的对象,审查的内容,因为他们想让人们无法确定他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
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对抗审查。一是利用替代平台进行曝光,但是我们不能只使用这个方法。我们还必须使用能接触到最多人的平台。例如,当罗伯特•马龙(Robert Malone)被审查,被从LinkedIn上被删除时,其他人也要抱怨,强调科学家参与辩论非常重要,否则会影响公共健康。所以,在他被LinkedIn删除后,我写了这篇Twitter文章。实际上这个屏幕截图是我今天早上做的。
如果你们能看到该推文的右边,他们正在建议我关注其他人。他们认为我应该关注LinkedIn,而我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还认为我应该关注罗伯特•马龙,我很乐意这么做。唯一的问题是,Twitter也暂停了他的账户,但是他们仍然建议我应该关注他。所以,至少,这很好。你们会注意到,当点击他的文章时,他们删除了他的简历,但在他的账户的广告上,简历仍然是完整的。
至于替代平台,我有时在GETTR、GAB、Parler和Speaqs上发帖,我在那里从未被审查过。还有Truth Social的新平台。我认为使用这些很重要,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使用现有的。我们也可以尝试跟人们开些玩笑。有一次我在《国会山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我觉得我不应该只是……也许如果我把它发布在Twitter上,会被审查。所以,我说,“Twitter不允许我,不许疫苗科学家自由讨论疫苗,但是你可以在这些其它平台上找到我。”
本周早些时候,我说,“在被Twitter审查后,我写有关口罩的文章必须要小心。”然后我说,“如果你做手术,请戴上手术口罩,你会保护病人。”我认为这是……没有人可以反驳的,不是吗?你是否同意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应该戴上口罩?你同意吗?好的,很好。我们都同意了。而且没有人可以说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
实施封锁来保护年轻低风险的人?让科学家闭嘴有点荒唐
在过去的两年里,作为一名科学家,经历的事情令人震惊。这有点荒唐。我们有NIH主任柯林斯和NIAID主任福奇,他们认为促进科学的方式就是通过发表攻讦文章让科学家闭嘴。这是非常荒谬的。我们看到一个遗传学家和一个病毒学家认为自己比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这几位)流行病学家更了解流行病学,并称他们是“边缘流行病学家”。
我们实施封锁来保护年轻的、低风险的和使用笔记本电脑的人群,而不是把保护重点放在年长的、高风险的人身上。这个错误导致了许多人死亡和许多不必要的死亡。还有人假装关心全球穷人,赞成封锁,封锁对世界各地的穷人造成的伤害仅次于战争和奴隶制。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惊人而且荒谬。
人们一直在指责这些反对破坏性封锁的劳动阶层是右翼极端分子,他们是这些封锁行动中承受打击最重的人,他们有过这种经历。我们看到有科学家在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上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质疑COVID康复后的自然免疫力。自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以来,我们了解自然免疫已经长达近两千五百年。毫无疑问,COVID康复后自然免疫力会很强,而且比疫苗免疫力更好。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会非常惊讶。
我们曾有一位疾控中心主任,他认为口罩比疫苗能更好地预防COVID。然后,又有一位CDC主任质疑康复后的自然免疫力。我们解雇了在COVID康复后获得自然免疫力的人,尽管他们最不可能将COVID传播给其他人。CDC也解雇了我,因为我支持疫苗,因为我过于支持疫苗。大科技公司审查那些对大流行做出了准确判断的流行病学家,反而把那些判断失误的人升格为COVID专家。
有时人们有点……这些COVID专家,有些人其实甚至根本不了解传染病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然后,我们搞了COVID清零,我不想谈论这个。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嗯,我们有辩论,而不是审查和诽谤。斯科特提到,我主动提出要和那些写这封信批评他的斯坦福大学98个左右教员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辩论,这个邀请仍然有效。如果你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请转告他们,我很乐意在这里或其它地方与他们辩论。
我们本应讨论如何更好地保护高风险的老年人。我们应该更多地讨论所有这些封锁的危害,以及由此带来的附带的对公共健康的损害,因为公共卫生不仅仅涉及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这些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在这次大流行中我们没有遵守。
我们必须信任公众,提供诚实的信息,否则他们永远不会信任公共卫生和科学,而这正是发生的事情。人们不信任公共卫生和科学是有充分理由的。我认为科学与自由学院的一个目标是要恢复它,使我们再次值得信任。这些是我对过去两年的评论。现在我想邀请我的同事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和杰伊•巴塔查里亚博士上台,并由《大纪元时报》的杨杰凯主持问答环节。
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https://www.youlucky.biz/atl
(未完待续)
《思想领袖》制作组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