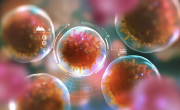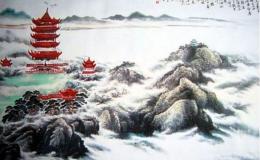从湖北大地上消失的人(四)
武汉兵变:真正的造反运动
1967-1968年,在毛号召夺权下,全国开始了武斗。在广州街头,人们杀红了眼,咬着匕首,抬尸游行。1967年初,各省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各级机关领导被戴上高帽、胸前挂上牌子游街;工厂停工、学校罢课,在毛的煽动下,军队、红卫兵、工人各方派系互斗夺权,各地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次在文革中震惊全国的事件。武汉军区与工人、红卫兵造反派发生激烈冲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武汉军队,激发了武汉军民的愤慨,一些百姓成立了“百万雄师”。不久,北京派来由王力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加激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19日晚上,两千辆车子在全城彻夜大游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天亮后,愤怒的“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蜂拥而入东湖宾馆,揪斗、殴打王力,把他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询问。当时毛就住在东湖宾馆,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安排毛乘飞机离开武汉。
这一震动北京的事件就是影响重大的武汉事件,也叫7.20事件。这是一次对文革的大规模抵制,它事实上是直接针对毛的指示,以及在这一指示下崛起的造反派而爆发的兵变。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事件直接冲击到毛的安危。
“在武汉720事件以后,毛完全被吓破了胆,因为当时这个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搞成了一场兵谏。毛这个时候吓破了胆。”(李肃《回首文革》)在全国造反背后做壁上观,做看客推手的毛万万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被卷入其中,陷入真正的危险。
“百万雄师”一号人物俞文斌回忆:“我们反对了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了毛。的确,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
对于毛的错误群起而抵抗的武汉兵变其实是一场大胆、出自于本能的兵变。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在人们能够正常思考,正常反应的状态下应该发生的事。整场由毛所推动的血腥十年文革,正是一次又一次由毛有心犯下的非理性、致命的“错误”,而自杀式的往悬崖边上推进。但如武汉军队和百姓这样冲冠一怒奋勇而起的,却如凤毛鳞角。而由于绝非偶然的巧合,武汉兵变直接冲击到毛的安危,更加深了这场兵变的历史意义。
武汉兵变发生在文革初始的时候。事发时吓破胆的毛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此后,造反派开始从军队那里夺得枪支,枪支落到了不同派系的手里,各地实枪实弹的展开了更加凶残的武斗。 “七•二〇事件后,湖北省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4万人。仅武汉就打死600人,打伤或打残6.6万人。”(《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湖北是最早成立独立政府的省份。在这里发生文革中真正的造反事件,也就是真正的对当权者大胆反抗的事件,不是偶然。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在辛亥革命前夕多达五千人,是全国第一。武汉人的脊梁中有一股无法弯折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催生了文革十年中震惊全国的武汉兵变。只要再朝前进一步,当年的武汉兵变就能在东湖宾馆把毛拿下,历史也将改写。
当然,历史按照既定的蓝图朝前推进。被西来幽灵绑架的中华民族注定得承受更多更大的苦难。这些苦难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千变万化,其中最深的苦难是人们竟然忘了自己是被一个外来政权所绑架,忘了这一切苦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他们承受的苦难也就更加的悲惨。
从湖北大地上消失的人
武汉兵变半世纪后,在武汉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
从2011年起,武汉陆续失踪了几十名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大多二十岁上下,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多是在长江大桥附近失踪的,有些是本地人,有些是远道从外地来武汉的。最起人疑窦的是,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不约而同,几乎都是在抵达武汉不久后就人间蒸发了。像是国土上的一个黑洞,武汉把人吸进去,就永远消失了。
当焦虑的父母要求公安调出摄像镜头录像带查看时,却被拒绝了,或者是告诉他们调查无结果。当询问为什么遍布武汉四面八方的“天网”竟然不能找到这些大学生的下落时,也得不到任何回应。相反的,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失踪事件不够立案标准。”警方并且警告家长不可接受采访。
“中国天网”工程是全世界最大的监控系统,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能让人民很有安全感”。在武汉一地就有90万个摄像镜头。然而正是在这遍布全国的天网下,这些身高一米八的大学生人间蒸发了,无迹可寻。

数十名大学生就这样在武汉失踪了。他们的父母们在国土四方东奔西走,许多年过去了,一无所获。这些孩子多是独子,是他们唯一的寄托。当独子终于长大成人,却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大陆失踪的孩子每年有20万人,有多少个失踪的孩子,就有多少对心如刀割的父母在这硕大的国土上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的四处寻找,如受刀割。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们成了访民。在遍布红色中国的巨大贪腐脉络中,百姓如海一般深的冤屈延申成一条漫漫长路。
在繁华的街上,一辆车里的广播器传来林少卿焦灼的呼唤:“请帮我们找一找儿子啊!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找不到啊!”20岁的林飞阳在俄罗斯留学,从俄罗斯偷偷回国,出了武汉天河机场之后就失去了消息。
一天夜里,林少卿和另一位儿子失踪的父亲在武汉相聚,两人不说话,只是叹气。林少卿像是对自己说:“怎么跟父母说,说‘爸、妈,我把你们的孙子搞丢了?” 说完,两个父亲在那辆跑遍国土寻找孩子的车里痛哭。
这样的父母还很多。2015年,湖北黄石市14岁的杨鑫在家门口走失,他的父亲骑摩托车行程7万多公里,最远到达西藏高原,一路上他风尘仆仆,寻找自己唯一的儿子,他的车子前后堆满了杂物。
“有时他也起身跑起来,跑到路口不停,靠本能拐弯,继续跑,好像那样他就能知道更多,好像跑起来就能得到正确的方向。有一天夜里他跑了很长一段路,起初喘不开气。后来忘了喘不开气,想停下来又连停的力气也没有,他记得他是摔倒了才停下,坐在地上,他往四周看,他不知道那是哪里,他就记得到处都是树,一个人都没有。他往那些茂密的树叶里看了很久。(《永失我爱:一个被拐十二年未归的孩子》)
这是湖北人孙海洋,2007年,他的孩子孙卓在深圳失踪,多年来他在全国四处寻人。一个失踪的孩子在父母的生命中划下无法治愈的伤口。同时,一胎化的政策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它在人们心理投下的阴影其实远远超出人的估量。当孩子,尤其是男孩成为稀有的珍品时,拐卖就成了逃避不了的罪恶。而当人们唯一的孩子被拐走,那就像是在他们心中挖掘一座痛苦无底的深渊。
一胎化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阴影超出想象。在这一意义上,红色中国是一座心的炼狱,在这些受尽折磨的父母身上,这座炼狱施行了独一无二的刑罚。